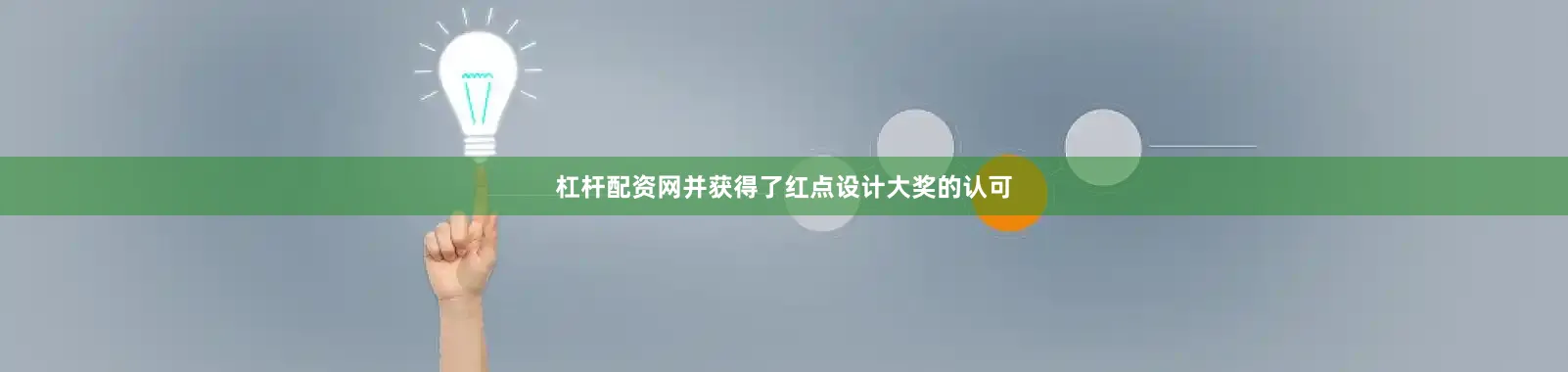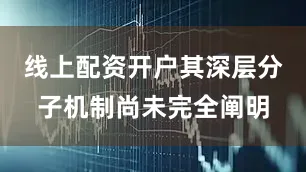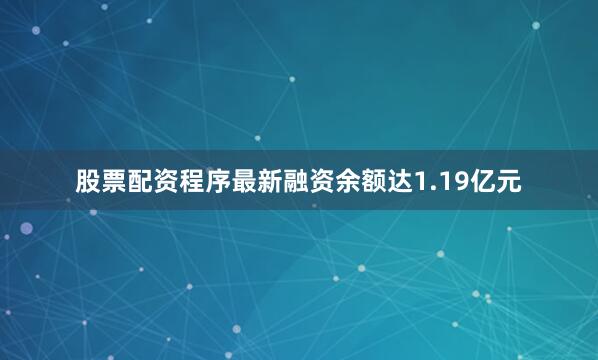1979年8月20日凌晨,东长安街还笼罩在清凉的晨雾之中,人民大会堂的灯却彻夜未熄。值班人员往返穿梭,口中念叨着同一个名字——张闻天。距离中央批准的追悼会只剩短短数日,一切安排都要在这几天内敲定,谁来主持、谁来致辞、规格如何,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反复推敲。
外界只知道,张闻天去世已满三年,中央决定为他举行单独追悼会,规格之高,罕见其匹。可真正让组织部门犯难的,却是致悼词人选:刘英先后两次向中央写信,郑重提议邀请陈云。但陈云本人并未马上松口,这其中的曲折,与张闻天半生沉浮的际遇一样,颇多波澜。
追溯因缘要回到四月。那时刘英从胡耀邦处获悉,中央已正式通过文件,决定为张闻天恢复名誉并举办追悼会。电话放下,她沉默良久,随后拨通了中南海总机,请求转陈云办公室。接通后,她用极低的声音说:“老陈,如果由你来说几句话,他会欣慰得多。”陈云隔着电话沉吟,最终答应考虑,但没立即给出肯定答复。

两人相识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上海。张闻天毕业于复旦,陈云来自青浦南翔,年纪相仿、籍贯相同,同走进了秘密印刷所与地下交通站。清晨跑步、夜里制版、偶尔打打乒乓,革命生活在紧张中带着年轻人的火热,当年的情谊就此结下。之后,他们在中央苏区共事两年,又一同经历苏区最艰苦的供给危机,对彼此的性格、能力、抱负知之甚深。
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张闻天与王稼祥联手支持毛泽东,使得正确的军事路线得以坚定推行。陈云当时虽身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但对此举极为赞赏,后来坦言这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抉择”。这种理念共鸣,奠定了两人几十年的深厚友谊。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云调回延安任书记处书记,再度同张闻天并肩。延安窑洞里,每到深夜,张闻天伏案起草《论抗日根据地的宣传与组织》,陈云则在坯墙另一侧准备敌后金融工作的材料,灯火交替照亮,映出两人的剪影。

1946年,东北局组建,陈云、张闻天先后到达沈阳。为了快速恢复铁路,张闻天多次走访修械所、机车房,陈云则负责统一财经,此后东北行政委员会体系雏形初现。根据档案记载,仅1947年上半年,两人连续调度的粮、棉、煤、铁等物资总量便突破三十万吨,成为解放军主力东进的补给保障。
正因如此,一旦提及张闻天,最了解其功绩、最能代表“老同志”群体发声的人选,人们自然想到陈云。刘英的请求也基于此。可陈云为何会在最后关头婉拒?
出现转折的是8月22日。那天午后,陈云顶着烈日步入刘英北池子寓所。简单寒暄后,他开门见山:“刘英同志,我很想站在灵柩前说两句,可是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已经点头——小平同志愿意亲自致悼词。”说完,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草稿递给刘英,“邓小平执笔,字字推敲,你放心吧。”
一句“更合适”,背后是政治分量的考量。1977年十一大之后,邓小平以副主席、副总理身份重回中央核心,主持拨乱反正工作。外界普遍关注他对历史功过的重新评价。若由邓小平站在追悼会讲台,无疑意味着中央最高层对张闻天一生的认可,也象征着新时期整党思想路线的延续。

刘英闻言,只是轻轻点头。多年拼杀、无数惊险,她早练就坚毅,如今却罕见动容。她收好邓小平的草稿,声音比蚊哼略高:“中央的决定,就是对闻天最大的安慰。”
8月25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肃穆庄严,挽幛上书“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同志永垂不朽”。送花圈的队伍在骄阳下延伸到公墓门口,各单位代表与老同志络绎不绝。
10时整,司礼人员敲响钟声。邓小平扶案而立,沉声开口:“张闻天同志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坚持真理,维护党和人民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三千字悼词,没有冗言,却层层递进,既提到他在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也回顾他在东北财经整顿、外交事务中的实际业绩。

在此之前,1979年初对部分受冲击的高级干部平反工作尚在推进。有人担心,单独为张闻天举办追悼会是否会引起“特殊化”议论。事实证明,这种担忧多余。对功勋人物的正名与隆重追思,是在昭示一种价值取向:党内历史是非终将厘清,贡献与过失会有客观公论。
值得一提的是,悼词结尾没有惯常的豪言壮语,只一句“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无私与坚韧”,便戛然而止。会场寂静,随后暴发出长时间低沉的抽泣声。对1945年入党的老兵、对1950年参军的干部,那些曾在无线电里听张闻天讲话的回忆,突然涌上心头。
为什么张闻天能获得如此高规格的追悼会?答案离不开三条主线:长征期间对正确军事路线的维护;延安时期对理论与宣传干部的系统培养;解放战争及建国初期对东北经济、对外外交的开拓性贡献。仅此三项,已足以将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奠基者的序列。
公开资料显示,张闻天一生至少三次“让贤”。1935年他主动建议毛泽东出任红军前敌总指挥;1943年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请求辞去书记处总书记;1954年又提出离开国家副主席的考虑,转而接受外交部副部长较次要的岗位。每一次转身,都是让自己的位置后退一步、让党的事业推进一步。

这种“不恋权”的品格,陈云比谁都清楚。当年在苏区,组织科名额紧张,张闻天坚持把机会让给更年轻的干部;抗战中,文宣口缺人,他同意调未婚的新同志进延安报社,自愿去条件艰苦的河北平原搞社会调查。回想种种,陈云才会觉得,“由更高的党中央领导人致辞,更能匹配他无私无畏的一生”。
一些研究者注意到,邓小平在追悼词中两次提到“忠于毛主席的建党思想”。此处措辞并非客套,而是历史映照。张闻天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配合,为红军摆脱被动奠定基础;延安整风期间,他在《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旗帜鲜明支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后期评价张闻天,“是个好同志,不贪权”。在党的高层关系错综复杂的岁月里,这句朴素认定弥足珍贵。
另一侧面,是张闻天的理论修养。1948年冬,他在长春用不到一个月写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纲要》初稿,提出“国营经济为领导、合作经济为桥梁、个体经济向集体化过渡”的思路。建国后的一五计划编制里,陈云对这一思路加以吸收,形成“调动农民积极性、国家控制重工业”的具体方案,直接影响新中国早期工业化布局。
外交战线的成绩同样不容忽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张闻天与周恩来密切配合,对主持会议的英国首相艾登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主要发言逐条反驳,争取了对朝停战后半岛局势的主导权。法国报纸曾用“沉着冷静的亚洲学者”评价他,足见国际舆论对其谈判技巧的认可。

然而身居高位并未改变张闻天的简朴生活。去世前,他住在棋盘胡同一处平房,每日晨起自己提水,读书写作到深夜。秘书回忆,他的白瓷茶缸沿口磕掉一圈釉,每次接待客人,只轻描淡写一句:“还能用。”
张闻天弥留时只留下一个请求:将余下工资与存款全部上缴作为党费,不留一分给家人。刘英握着他的手,哽咽却没掉泪。这个请求看似简单,却直指“公私分明”四个字,也用行动为后辈树起标杆。
追悼会结束后,陈云在日记里写道:“闻天无意功名,却得大名;无心权势,却赢民心。”短短十四字,点明了他的历史定位。

当年的八宝山礼堂,如今墙面上的旧木纹依稀可辨。档案馆里保存的追悼会影像,仍可看到刘英在角落里握紧手绢的瞬间。时光流逝,留下的意义却未褪色:一个革命者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站在舞台中央的辉煌,更在于离开镁光灯后仍坚守的原则。
从张闻天的轨迹,看“让贤”背后的政治智慧
张闻天以“让贤”闻名,却并非因懦弱或退缩,而是深知大局需要,在合适的节点果断退位,把更适合领航的人推向前台。如此举动,在政党史上并不多见。 1945年6月,七大闭幕后,张闻天主动向中央写报告,请求不再担任书记处总书记。这一做法在当时颇为罕见,因为党正处在转战东北、筹划全国战略的关键期,负责书记处工作的地位举足轻重。 为何选择这时“让贤”?首先,战争形势急剧变化,军事指挥与战略决策更加倚重前线经验,而毛泽东在延安的指挥位置凸显权威,需要更集中统一的领导;其次,经过整风,全党思想趋同,继续保留一个书记处总书记层级,容易造成指挥链冗余。张闻天深谙组织原则,主动退出,既避免权责重叠,也为毛泽东进一步整合依据提供了便利。
第二次“让贤”发生在1954年宪法颁布后。那时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相继确定,副主席人选讨论时,有同志提议保留张闻天。对此,他诚恳陈述:“外交工作刚起步,需要精力;副主席更需面对全国事务,我恐力有未逮。”短短一句,既表态也给中央一个“优化配置”的台阶,最终,他如愿进入外交部。
第三次在1962年初春。苏联中断贷款,国家经济出现困难,张闻天建议设立“经济检查小组”并自告奋勇去基层调研。外界多认为他志在重返中央财经领导系统,但完成调研后,他却坚持要求改调其他同志负责小组,自身留在国务院小范围咨询岗位。此举帮助中央避免了“救火队”人事频繁更迭的麻烦。
透过这三次“让贤”,可以梳理出张闻天的政治智慧: 1.主动识变,揣摩大局。他懂得,决策链条越精简,越有利于统一指挥。 2.保持自省,避免权力沉淀。长期占据高位,难免产生路径依赖,他以“退”缓解组织惰性。 3.用退步换取整体前进。放弃一己职务,却促成更合乎形势的班子组合,这是一种服务整体的战略。 研究近代史会发现,一个政党要保持活力,就必须在不同阶段选出最合适的“冲锋者”与“中军”。张闻天的“让贤”不是简单的谦让,而是对自身角色与历史节点的准确把握。 今天阅读档案,依旧能感受到他在那份《自请辞职报告》中写下的冷静笔触:“个人去留事小,路线得失事大。”这句被反复引用的话,至今仍是衡量领导干部境界的标尺。
查查看股票配资,配资之家平台,深圳知名的配资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国内正规配资公司新车将会是一台五门车型
- 下一篇:没有了